阿舍谈《阿娜河畔》:
打开自我,面向辽阔的历史和生活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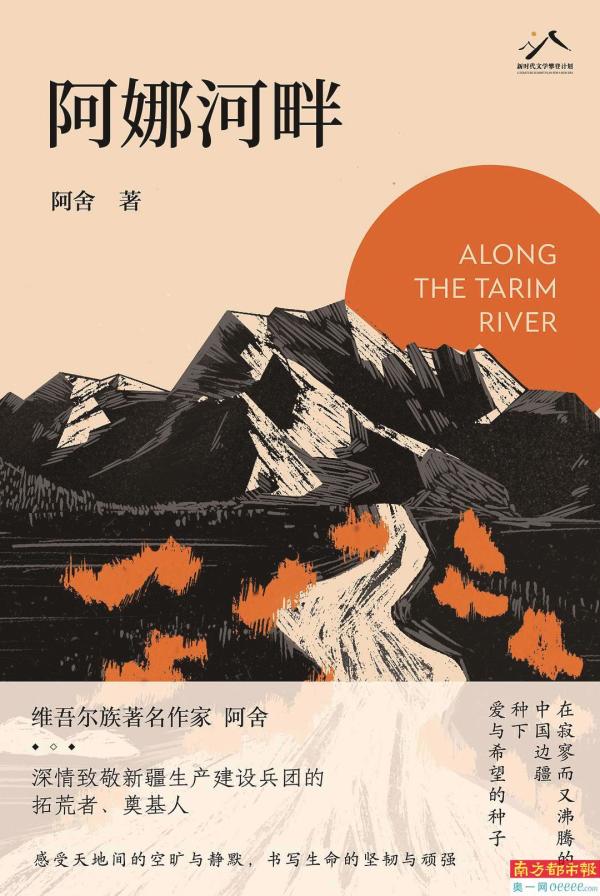
《阿娜河畔》,阿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版,68.00元。
“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里是“母亲”的意思。小时候,在阿舍家居住的农场场部有一条人工渠。“大渠的水引自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在农场的东南方。从大渠引向各个生产单位的毛渠如同农场这个有机生命体的毛细血管,为各个居民点、各处耕地、林场、畜牧点带去宝贵的饮用水。”阿舍回忆说。塔里木河的河水哺育了农场上的生命,为无垠的沙漠增添绚丽色彩,“只要水流到的地方,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维吾尔族著名作家阿舍的长篇新作《阿娜河畔》今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阿娜河畔》讲述了在新疆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小说多角度、多方位地描写了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以及边疆人民生活的跌宕起伏和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可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后,展现了几代人在边疆的建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
该书以阿舍的故乡为原型,书写波澜壮阔的兵团发展史、农场建设史,是阿舍对自己的父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拓荒者、奠基人的致敬之作。
阿舍是兵团二代,周围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她的母亲却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2008年,阿舍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的散文《黑蝴蝶,白蝴蝶》获得《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在那篇早期作品中,阿舍笔下的故乡和童年蛮荒、粗糙而凌厉。2016年起,阿舍开始专门搜集与兵团有关的资料,农业、工业、教育、水利、科学、医疗,文学创作、口述历史、纪实采访、学术分析……故乡于她而言不再是记忆里的零散碎片,两代边疆建设者的不同遭遇让她对兵团历史有了更完整的认知。
阿舍告诉南都记者,在阅读第一代农场建设者的史料时,她经常要放下书本长出一口气,“经常要问一句,他们身上的那种坚韧和乐观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打开自我面向历史和辽阔的生活之后的最大收获,看到了更丰富的人心与人生。”有别于《黑蝴蝶,白蝴蝶》,《阿娜河畔》的故事虽起伏跌宕,笔调已变得朴素、明澈和舒缓。在这部小说中,阿舍首次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变成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那些令人欢笑与哀哭的命运故事之下,历史如阿娜河水般缓慢而宽阔地涌动。
专访
南都:请谈谈你真实的故乡,你出生和成长的兵团团场和周边无垠的沙漠。在这一刻,当你回忆它的时候,最为难忘的是什么?
阿舍:我几乎就是按照个人记忆在小说中还原了故乡的地理样貌。一条人工修筑的大渠流经农场场部,在小说中,我将这条渠命名为茂盛渠,实则它没有名字,就叫大渠。大渠的水引自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在农场的东南方。从大渠引向各个生产单位的毛渠如同农场这个有机生命体的毛细血管,为各个居民点、各处耕地、林场、畜牧点带去宝贵的饮用水。农场耕地和居民点分布极不规则,各生产单位分布在库若公路的南北两边,或远或近,南面的可耕地多一点。居民点非常少,场部是人口最集中的一块。农场场区之外,便是戈壁与沙漠,近河的沙丘之间,会有地下水渗出形成天然湖。农场虽为戈壁与沙漠所包围,冬春两季的色彩虽然极其单一,哪里都是浑黄一片,世界仿佛只剩下天蓝和土黄两种颜色,但夏秋两季,尤其夏季,渠水、植物和农作物会让农场的景色大为改观,只要是水流到的地方,都焕发出勃勃生机。无论什么时候回想农场,最难忘的就是与水有关的夏天,烈日、渠水、植物、鱼群、水蛇和笑声,另外就是我知道的邻居们,上海人、四川人、天津人、北京人、河南人、山东人、湖南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不停地回闪。
南都:《阿娜河畔》里的茂盛农场是以你的故乡为原型吗?它与你真实的故乡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阿舍:文学从来不会等于现实,我认为即使是非虚构写作,比如散文,比如纪实文学,甚至报告文学都不会完全等同于现实。因为文本里的叙述者在开始叙述的一刻,他/她已经离开了事件发生的现场,他的叙述已经与现实产生了时空上的距离。即便要求叙述者尽可能做到最大化的客观,他的写作仍然带着主观的感受、判断和想象,他使用的语气、词汇,都包含叙述者的主观取舍。从这个意义上来打个比方,现实就是飞机场的停机坪,文学文本则是在天空中飞行的飞机。茂盛农场脱胎于我对农场的记忆,除了样貌和历史脉络有所参考,里面的人物故事都是经过文学提炼和想象的,农场人的生活细节、劳动过程虽然被尽可能地予以还原,但主要人物的人生、性格与命运完全是重新创造,在这一点上,几乎与现实中的故乡没有可比性,茂盛农场属于一个虚构的文学世界。
南都:你在创作谈里提到为了写这部小说,查阅了整整五年的相关文献资料。请谈谈具体查阅了哪些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感触?
阿舍:长篇小说创作者为长篇而进行长时间的构思和准备,应该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它其实不值得过分去强调。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兵团层面的分类史,如兵团教育、兵团水利;兵团史料集成,这一部分分得更细,如解放新疆史料、早期妇女进疆史料、知青进疆史料;再就是各团场史志丛书、个人口述史以及专题论文等等。
在查阅文献资料之前,我对农场的记忆大多是零碎的、片断式的、更个人主观化的,关于农场的历史完全是一知半解。在查阅文献资料之后,我对农场的认知空间大幅拓宽,像小说中明双全这一代1950年代进疆的第一代建设者被拉进我的视野中,之前,只是在父亲和邻居聊天时零星地听到过一两句,但在文献史料中,他们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的人生因为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生产运动,因此异常的丰富、艰辛和惊心动魄。简单来说,查阅文献资料之后,我对小说最初的构思已经不成立,因为最初我是打算从改革开放写起,有了对农场历史的完整认识后,小说的时间就从20世纪80年代前移到了1950年代初期。这个调整是迅速做出的,也因此给自己提出了更大的难度,因为这增加的三十年,我几乎是没有记忆的,完全要靠更多更详细的阅读、思考与理解去填补,再靠文学的想象去创造。
南都:《阿娜河畔》写了两代边疆建设者的人生故事,呈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存在与付出,艰难与坚守,悲喜与挣扎”。你也曾经说过,兵团团场里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既是开拓者、建设者,也是一群“惊慌失措的时代流亡者”。时隔多年,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怎么评价他们的命运?
阿舍:这个问题其实藏在上一个回答中。“惊慌失措的时代流亡者”这句话出于《白蝴蝶,黑蝴蝶》这篇写于2008年的散文,那时候我对农场的记忆都是零碎的、片断的和更主观的,那时候的我,因此在回望故乡、在书写故乡时,取用的都是童年、少年的个体生命经验,那些经验对农场的认知还局限于自己熟悉的人与事、自己记得住的人与事上。具体来说,“惊慌失措的时代流亡者”,更多是指1966年以后进疆的内地知识青年,这一批知识青年与1964年甚至更早来到农场的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他们中更多是因为出身不好、是因为家庭遭受变故被“要求”来到农场的,而1964年甚至更早的那一批知青,很大一部分是自愿,是出于对建设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时代号召的强烈回应自愿前往农场的。在我的记忆里,因出身受牵连、被动来到农场的内地知青也有相当一批人,他们有的是我的邻居,有的是我的老师。我母亲本身也因为出身问题从师部机关下放到农场,临近退休才重回师机关。从自我的生命经验出发,这批人的人生给了我更多记忆,所以,在不了解更多农场历史之前,“惊慌失措的时代流亡者”就成了我的记忆主角。
总的来说,虽然来到农场的出发点和原因不一样,虽然有人是自愿的,有人是被动的,但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共性——不强调或者放弃自我,尽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地服从国家意志、集体意志,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集体大于个人,不鼓励、不支持、不突出个体与自我;后来我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人性的戕害。所以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开始迅速回到自我,更多地回到自我,直到新世纪到来,更多人又陷在精致的利己主义和封闭的个人主义当中,可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在《阿娜河畔》的写作中,放置了自己的这个思考——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到底哪一个选项能让我们自身、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在小说中,我让被时代洪流所裹卷的成信秀、明中启、石昭美等人努力地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试图通过他们,为自己的思考寻找一种通过的路径,但仅仅是试图,我觉得我的思考还在不断向前摸索,《阿娜河畔》只是其中一段。生命与文学创作,从来就是共同生长和成长的,一段有一段的风景,一段有一段的思考与表达。
南都:这部小说里你个人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个?为什么?
阿舍:我最喜欢李秀琴,应该说,最心疼李秀琴。因为她的爱最无私,因为她身上的母爱填补了我生命里的空缺,她像是沙漠里一股甘泉,慰藉了她生命中所有靠近她的人,她的早逝体现着她的疲惫,即使是最爱她的亲人们,也没有想到尽早回馈她的付出。
南都:和以前的写作相比,《阿娜河畔》带给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阿舍:有两点。一是把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变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此之前的创作,多发于自身的个人记忆,对故乡的呈现是零碎的、片断式的,故乡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在作品中,人物的出现与发展没有和历史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到了《阿娜河畔》,对农场建设史的呈现是其主题之一,但通过文学讲历史,搞不好就会让文本陷入宏大叙事的陷阱当中。所以要反过来,通过人的故事、人的命运来体现历史。虽然一开始就明白这是创作原则,但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感到困难重重,尤其在呈现时间流逝时事变迁的过渡段落里,如何把大历史隐藏在叙述当中,确实很考验人。
另一点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气”。前几天在《阿娜河畔》的宁夏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读完《阿娜河畔》,欣慰于小说的“气”足够绵长,支撑到了最后,但阅读过程中,他其实很担心,这口“气”如果坚持不到最后该如何是好。我想这是写过长篇小说的作家的共同体会与经验。在创作中,尤其写到后两章,每天提笔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气”是什么,简单地说,至少包含热情、信心和体力这几个方面,要让这几个方面天天保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上,真的非常难。好在《阿娜河畔》完成了,只是,偶尔回想整个创作过程,会有些后怕。
南都:以后还会写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吗?你认为兵团团场的独特历史还有哪些尚待探索、书写和揭示的部分?
阿舍:故乡题材是我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我希望今后自己的视域会更加宽广,希望在《阿娜河畔》之后,能够继续有所表达。事实上,我愿意把整个新疆视为自己的故乡,在《阿娜河畔》之前,我还有另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乌孙》。从2012年的《乌孙》到2023年的《阿娜河畔》,从两千年前的汉朝到两千年后的20世纪后半叶,跨度之大是我自己无法预料的,所以,下一部,如果再写故乡,她会是什么面目,对于我自身而言,都是未知的。但兵团发展史、农场建设史,显然还有更多值得书写的内容,如果要写,一切皆有可能吧。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