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书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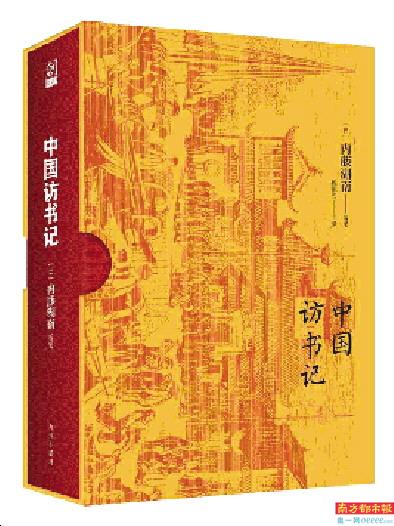
《中国访书记》,(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7月版,138.00元。
□ 姚一鸣
《中国访书记》一书选了内藤湖南(日本记者与学者)、田中庆太郎(日本汉籍书店文求堂老板)、岛田瀚(日本书志学家)、吉川幸次郎(日本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日本帝国大学学者)、武内义雄(日本学者)、长者规矩也(日本学者)七位来中国访书的记录,再现了清末民初图书市场和古籍收藏的状况,还原出日本学人或书贾在中国搜罗古籍的记载。
在译者钱婉约的《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中国访书记》附录)一文中,对于学者专家、书贾等来华访书进行了总体论述,并对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长者规矩也六位的生平及访书购书基本情况予以了介绍。也阐述了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钱婉约在文中写道: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近代日本学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80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以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这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
译者钱婉约对于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活动,显然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析。其实内藤湖南的奉天访书,对于沈阳故宫满蒙文档案文书的摄影,也是介于学术交流与文化掠夺之间,那个时代社会动荡,很多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开展,更没有意识某些东西的学术价值。“但日本人却为此特地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就不能放任不管。”作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的内藤湖南,显然在这方面起了开创性作用。
至于日本学人岛田翰,就不得不说到著名的陆心源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事,陆心源之子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而导致出售藏书,首先考虑的是国内公私卖家,但商务张元济等多方努力未能如愿。张元济在《致缪荃孙书》中曾经曾言:“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予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竞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版)最终陆心源皕宋楼藏书以10万元之价全部售予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其中有旧藏珍本4146种,合计43218册)。据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载:“今兹丁未(1907年)三月,成斋先生有西欧之行,与树藩会沪上,四月遂订议,为十万元,五月初二,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岛田翰在这次售书中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其一是多次到江南考察这批藏书的版本价值,并受静嘉堂之托与陆家洽谈﹔其二是促成了这次交易的成功,作为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深知皕宋楼藏书的价值﹔岛田翰也是这次收购的中间人,和买卖双方陆家、三菱岩崎氏都有着较好的关系。皕宋楼藏书出售予日本之事,在当年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诸多有识之士对汉籍外流都痛心不已,藏书家董康曾言:“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事,和汉籍在当年的外流东灜,如果本着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仅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巧取豪夺、据为己有实非君子所为,和文化交流的宗旨是相差很远的。
由《中国访书记》想到另一本书,即古吴轩2014年7月出版的《苏州日记》,全名为《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作者高仓正三毕业于京都大学,任职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其师是京都大学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同一研究所的吉川幸次郎为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的弟子。1939年日本外务省派遣高仓正三为中国特别研究员,长年驻守苏州,主要任务是学习吴方言,尤其是苏州方言,了解吴语文化,搜集江南古籍文献。在其所写《苏州日记》中,记载了许多苏州当地的饮食及习俗,经由日常生活费用及购买书籍支出,反映出其时经济凋敝、物价腾贵的状况。作者曾对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带进行过长期游历,书中对其经游地的交通、民俗、经济、古迹古物(包括古建筑、碑刻、摩崖石刻、古钱币)、美景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和评价。
高仓正三派遣来中国之时,正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侵华之时,所游历和居停之地,都处在日本军队控制或傀儡政权统治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派遣高仓正三赴华的目的,和他的政治态度,是进行文化交流的学子,还是窃取搜集江南古籍文献的“特务”,是有不同看法的。需要说明的是高仓正三日记1943年在日本弘文堂出版时,即删掉了部分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古吴轩出版社翻译出版时,又大多撷取了日记中的访书内容,这种有意的规避,使人猜测一个战时日本学人的赴华,怎能完全置身于战争环境之外。其实从日记中高仓正三访书求师屡屡受挫(如郑振铎的多次避而不见),是可以看出些端倪来的。
关于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钱婉约在《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最后部分的阐述,是客观中肯的:“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 上一篇:海明威与西班牙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