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凋零处见盛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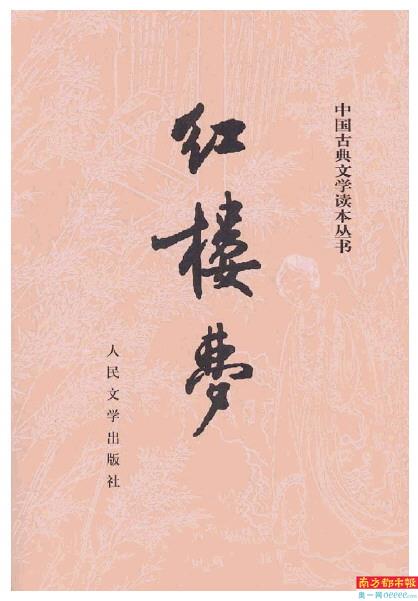
◎作者:华师附中 高一(3)班 曾舒蕊 ◎指导老师:赖慧
已是初冬了,岭南的空气里终于褪去夏末的余热。
我抱着书行走在向晚的校园,风温柔地吻着叶。仰头时叶在空中飞旋,远处是融作海棠红的天。世间仿佛只我走在这条小路上,一人驻足聆听秋的浅吟低唱。风深长,路过明灭的怅惘,辗转于红楼惊梦的时光。
且不道红楼如何开场,毕竟到头来终一片白茫茫。鲁迅更以“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形容它,不同境遇的人从中品出不同悲的况味,而我独倾心于黛玉之悲。
作为绛珠仙草转世,黛玉的自我完成便是报神瑛侍者的恩,还人间一世的泪。还泪,早已奠定了她生命中悲剧的底色。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少有人愿走黛玉的生命道路,这条路太孤单,也太决绝。譬如周瑞家的送宫花来,她得知是剩的就掷了回去。只给她一人的就要,旁人都有那算了。这折射出她的生命必须是绝对的、惟一的,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她注定要碎的,因为不要半分杂质。
葬花如是,她宁将芳菲掩于尘泥,也不愿其流入世俗中去。焚稿断痴情亦然,她以最孤绝的方式斩断了与人间的联系,直至香消玉殒。“个性的悲剧即宿命的悲剧“,何况她的个性与腐朽森严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对立。
晚风生凉,在我身畔迂回。过往千般美,最终埋葬时便有万种悲。
那一缕芳魂就此消逝在风中了么?若如此,百年以来黛玉的文学形象为何又如此鲜活?
过于圆满的落幕是不真实的,命运的曲折更凸显出人的品性,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个体。
这样一个惊才绝艳的女子连陨落都尚且是美的,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却赤裸裸地将生活中的庸俗琐屑摊开来,将她所有青春活力慢慢腐蚀给人看。
当爱玲的笔触到七巧这样一个“审慎与机智“的疯子时,我为之震颤。她被迫嫁给残疾的姜二少后,在阴暗的尔虞我诈中压抑了三十年,最终成了“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惨。她的窗外永远是“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如她人生的苦难。
循着这苦寻散落的碎片与零星的“甜”,“甜”只剩她对小叔的短暂真心,即使是一段夹杂着算计的薄情。
我渐渐将碎片拼作完整的七巧,一个受封建摧残至死的女子。若我将悲剧比作一场枯萎,那么她彻底枯萎的瞬间,却成了这个人物文学意义上光华初展的时刻。
苦难如隧道一般在她的人生轨迹中延伸,将边界不断延展,内在不断发掘,让我得以钻入她灵魂的深层,去感知她的爱恨情仇,去捕捉她藏在黄金枷下的闪光点。
黛玉与七巧的悲凉多源于一种执着,执着于对命运的反抗与不甘。而正是这弱女的不甘,被强悍残忍的现实碾压时,才成就了惨烈中的凄美感。
她们的结局在世俗眼中,皆是缺憾,但在文学意义中,却属于人物个性的净化,亦成全了另一种形式的纯粹与完整。
向晚时分,瑟瑟寒风又起。
只是叶落纷飞,四下无人语。
我依然抱着书行走在万物凋零的校园,仰头却蓦然发现,那是另一个盛放的冬天。
- 上一篇:谁不想要一个这样的外婆
- 下一篇:建党百年 青春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