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科医生出版首部半自传体小说
麾下谈《补心》:打开“白色城堡”,探求生命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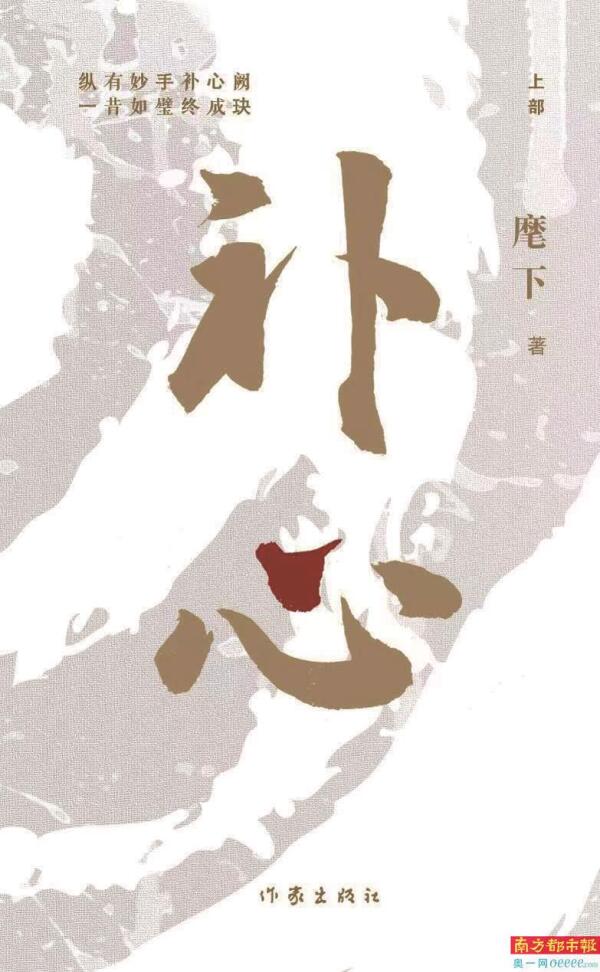

“如果医学是一顶王冠,心外科和脑外科就是王冠上的两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心脏还能开刀,怎么开刀?老百姓觉得非常神秘。这部小说从老百姓的视角做一个由浅入深的描述,打开神秘的‘白色城堡’,看一看里面玄奥的风景。”麾下微笑道。
麾下是国内心外科顶尖专家,北京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学医、行医四十三年,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派赴美国宾州医学中心、克里夫兰心脏中心研修;擅长心血管和肺血管疾病的外科治疗,曾创造肺动脉肉瘤术后世界最长存活纪录。
两卷本70万字的《补心》是麾下的首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甘隆出生寒微,靠苦读找到一条出路。他考取黄冈中学,继而升入医学院校,终于成为一名心脏外科专家。当与少时好友乔婕再重逢时,他庆幸自己多年的砥砺奋进而亟有所应——乔婕罹患罕见恶性肿瘤,甘隆竭尽毕生所学,全力救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医学奇迹。
所谓“专业人说专业事”,主人公如何攻克罕见恶疾肺动脉肉瘤,是《补心》一书的一大亮点。麾下告诉南都记者,原本自己的专长领域是在肺动脉栓塞手术,这个手术“全世界能做的大夫合起来可能就二十来个,国内当时我是最先开始,也做得最好。”结果肺动脉栓塞病人全都来找他看病,其中混杂着一种特殊的病人,患的是肺动脉肉瘤,几乎全都被误诊为肺动脉栓塞。麾下说:“我一个人前前后后共诊治了肺动脉肉瘤50多例,而这个病自从首次被发现到目前为止的一百多年间,全世界文献也只有200来例。”
《补心》一书中的乔婕的现实生活原型,正是麾下接诊的一位患者。肺动脉肉瘤患者生存期原本仅半年左右,因麾下果断地主刀进行了肺动脉内膜剥脱术,既将肉瘤剥除干净,又最大限度保存了身体正常组织,为病人又争取到整整七年的生命。该患者术后在美国斯隆肿瘤医院和安德逊肿瘤中心化疗成功,震惊医学界,两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也由此名声大噪。在美东肿瘤年会上,麻省总医院的医生甚至惊呼:“这个案例是我见过的第一例活着的(肺动脉肉瘤)病例!”
由于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来自麾下的真实生活经历,读起来曲折动人、跌宕精彩。在书中,既有一位小镇做题家“逆风翻盘”的开挂人生,也有一位医术精湛的心外科医生争分夺秒、赴汤蹈火的日日夜夜,更有患者面对病痛折磨时不屈的求生意志。生命的脆弱和顽强都得以纤毫毕现地展现,启发读者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更冷峻严肃的拷问。
作家张平说,“看了《补心》,觉得作者有可能是作家中最好的医生之一,也有可能是医生中最好的作家之一。”“大爱在人间,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展示的那样,‘补心’,既是爱心的审美圭臬,也是情感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医学工作者对人生的体验总结。”
专访
写了四千六百多首古体诗和现代诗
南都:《补心》里的主人公甘隆很小就开始写诗,动不动就即兴抒怀。您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文学?
麾下:您的提问十分敏锐,说明您的眼光十分犀利,也让我自己发现我尚不自知的写作当中的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我笔下的很多人物都爱写诗。
关于诗歌,有些网红讲师是能讲不能写,而我是能写却不太会像网红讲师那样渲染,但其实我平时已经积累写了四千六百多首古体诗和现代诗,虽然这些诗歌都没有发表,但它对我来说己经成为一个敝帚自珍的宝藏,因为其中很多诗被我不知不觉而陆陆续续地用进了小说创作当中,因而就形成《补心》主人公甘隆爱写诗抒怀的特点,我的其他作品当中的主人公也有这个特点,甚至在我的另一部未出版的关于五代十国的著作中,契丹王耶律阿保机和国师韩知古也都爱写诗。而且,我写的这些诗还常常被用于小说情节构成的发生、发展或转折当中。
我学知识讲究学以致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对古典文言文很感兴趣,所以我的小说语言就有点带文言意味在里面,虽然小说的叙述也是大白话,却使得我的写作带一点文言用词,从而显得比较有书卷气,我回读自己的文字时,感觉有点像啜饮醇厚浓香、带有太阳味道的红茶一般。
现在再说到我对于文学的喜爱。受兄长的影响,我小时候就爱读小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到新华书店去,一分钱一天租小说看。我父亲带着夸耀的神情指着我对他的同事和朋友说,你们看,我儿子这么小就这么爱看书。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文理科我都不错,但是那个时候考虑到将来搞写作可能没有搞理科那么顺畅,也就是就业不会太顺利,所以我还是选择读理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以数学、物理和总分三个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黄冈中学的。
南都:《补心》这部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麾下:困难和挑战是肯定有的,因为毕竟我是心外科大夫出身,而不是专业作家。我经常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将两个情节怎么衔接,怎么把它表述得更好,或者怎么让它出彩?
可能您已经注意到,我的写作是用一个热点接着另一个热点,但是怎么提高普通读者的兴趣?我感到有些难度。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头来讲一讲我和大家写作的方式的不同。别人都是在电脑跟前打字或者拿笔在纸上写作,我不是这样的,我基本上是在散步时间、业余时间写。比方说我散步的时候,拿着手机打开一个APP直接口述。我心里有想法就说出来,录音直接转为文字,我回家后就将文字导入到电脑里成为文档。我觉得非常奇妙的一点是,我在家里卡壳写不出来时,走在路上时常常突然灵光一闪,想法就像河水决堤一样地来了,往往几百字或者甚至几千字就这么写出来了,甚至有时候在一天之内上万字就写出来了。
当然这些文字中可能里面有很多错讹,但是它已经把我的思路打开,我回去在电脑里面把错字改一改,把缺的部分补一补就齐了,卡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写作还有个特点,就是如果头一天卡壳了,第二天凌晨睡觉醒来,就常常来了个灵感大爆发,很多美妙文字就涌现出来了。有了这些创作特点,所以我写作速度非常快,这部小说是从2022年8月25号开始到2023年2月15号结束,总共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初稿和修改工作。后来,书稿很快被作家出版社接受了,基本上也没做过什么大的修改,除了有矫正错字之外,没有情节上面的大改动。我的朋友、评论家曾祥书曾经担任过文艺报的编辑,他最近评论说,《补心》的写作特点就是在情节安排上大开大合,将网撒得开,也能收得回,有着开合有度、痛快淋漓之感。
常感到生命的脆弱 也感到生命的坚韧和顽强
南都:心外科大夫是不是整天要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
麾下:我现在当然比以前放松一点,虽然我现在还在继续工作,但是以前我在做一线心外科大夫时,尤其在当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时,我手机从来不敢关闭。而且我是住在医院旁边,从家里到医院下个楼上个楼几分钟就到了,很快就能到达急救现场。
因为我们心外科经常是这么一种状况,你刚刚看那个病人是好好的,一扭过头他可能就突然发生心跳骤停。所以我们都不敢住得离医院太远,尤其是刚刚做完手术,一定要在病人旁边逗留很久,以确保病人血流动力学平稳,尿量足够,出血引流量少。
我经常形容我的一个动作,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如果病人引流多、尿少、血压低,我就坐在病床边,两手拿着两根管道,一根是导尿管,另一根是出血引流管,带有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监护仪,病人血压向下走,我的血压就高起来,赶紧站起来调整药物的剂量和速度。尤其在早年的时候,我对危重病人一守就是守护一整晚上。那时我们是压力非常大的。外科大夫做手术之后,最怕病人出事。说实话,病人做手术,最希望病人好的就是给他开刀的大夫。
南都:做了一辈子的外科大夫,对生死、对生命是不是跟我们有不一样的理解?
麾下:说实话,作为心脏外科医生,我们看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觉得,做人太不容易了。我经常跟别人说,做人每一天都不容易。每到睡觉前,我就对自己说,还好,我又多活了一天。尤其我看到有些病例抢救不过来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幼儿,患有非常复杂的先心病,尽管手术成功了,但因为心功能太差而在术后发生严重低心排综合征,孩子没救过来。我在当时还不十分难受,后来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到内蒙古去,那天晚上坐在车上,天完全黑了,我坐在副驾座位上,朋友在开车,我突然想起这个孩子。车开一路我就哭一路,眼泪一直流。
后来在视频上看见有个美国一个大夫做完手术失败后,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哭,我非常能体会他的感受。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健康地成长、生存,直至终老,要遭遇到非常多难关和考验。那天晚上我在草原的黑暗当中,我想起这个孩子,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后的事儿了,仍然让我泪流满面,我当时想,他这么小,还未曾真正地展开他的生活,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生动可爱的世界,要是能将他救过来该有多好。这件事大概也有二十多年了,究竟是哪一年我也忘了,但是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此,作为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我们比常人有着更多直面生死的机会,这种直抵心扉的对生命的诘问常常是让人无可回避,也无处可逃!面对着生命的诘问,我既感觉到生命的脆弱,也感觉生命的坚韧和顽强。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更要把那些身外之物看淡,而将生命的历程、生命的真实感受和生命的过程看得更加珍重。我们的每个平常的日子,我们一颦一笑,甚至带有痛苦的欢乐,那都是生命的馈赠,也是对生命的礼赞。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