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黄金之路
□ 文/马胜佼(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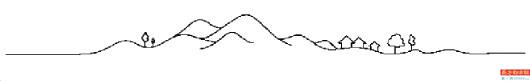
写给天堂的一封信
父亲1948年出生于湘中南一个异常偏僻贫穷的小山村,那时候自然是吃不饱的,但爷爷还是咬紧牙关送他读书,据说父亲的成绩每次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半工半读到了农业中学一年级,爷爷实在熬不下去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这时已经很明事理了,扛起比他还高的锄头默默跟在爷爷的身后,开始了他的修“地球”生涯。
用山里话说,父亲也是“吃了墨水”的人,虽然大山的粗茶淡饭铸就了他山一样的体魄,让他硬是在大山贫瘠的土地上淘出了一大家人的口粮,娶到了老婆,还养活了四个儿子。但他终究是不安分的,他说他可能走不出大山了,但他不希望儿子们的脚步永远停留在山旮旯里,于是他拼了命地送儿子们读书。别人家的孩子在清晨哭泣,那是因为想读书大人不让读了,我们家的孩子在深夜哭泣,那是因为说不想读书被父亲胖揍了。摇头晃脑中,我高中毕业了,却以年级“尾元”(年级最后一名)的身份名落孙山。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想出了新法子,安排我到海拔5000多米的矿上挖金。被盛夏高原的寒风和冰雪摧残了半个月后,我终于毫无廉耻地说出我要读书。后来,我成了我们那条山沟里的第二个本科生,第一个是我大哥。
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金”字,母亲的名字中有个“黄”字,或许这就注定父亲一生中和黄金总会扯上瓜葛。大约在我十岁时,一个山民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头上发现一棵倒树,连根刨的时候看见了金光闪闪。从此,这处不为人知的小金矿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父亲迅速行动,聚拢了一帮人,沿着金路挖洞,为了节约成本,金洞通常刚好够一个人的高度,两个人的宽度,碰到有的地方有大石头,就在边上凿个半人高的小洞绕过去。为了抢在别人前面,男人们通宵达旦地挖洞,挑矿石,妇女小孩做饭送饭,挑回的矿石放在机器内搅碎,在机器下架一张斜床,床上铺一块粗糙的布,放水由上往下冲,比重小的沙子被冲走,比重大的黄金留在床布上,耀眼的光芒辉煌了山里人的生活,也刺激了山里人的贪婪。高峰时,那个小山头上有数十个矿洞在同时推进,爆破声此起彼伏,由于安全意识极其淡薄,炸伤,塌方等事故不时发生,羊肠小道上,不时会有一具白布包裹着的遗体被抬下来。父亲也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一块大石头擦着他的头皮砸在脚背上,砸断了动脉,鲜血瞬间就标了出来。
两三年的疯狂,父辈们有了原始的财富和技术积累,只是这份积累来得过于血腥。那个山头被直接劈去了一半,小金矿的喧嚣也走到了尽头。
父辈们开始走出大山,在一些更为偏远的山区承包一些小矿尾矿开采,大额的投入,太多的不可预见,让淘金这个行当充满了高度的刺激和风险。父亲经历过一元钱的投入,三个月后变成十元的高光时刻,也经历过投入数十万,带回家的只有几个钢镚的血本无归。记得亏损最严重的那次,他从遥远的新疆,在绿皮火车上颠簸了几天几夜才回到家,灰头土脑,面如死灰,但看到我们,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从他的包中掏出了带给我们的哈密瓜干,至今我仍记得那浓浓的香甜和饱满的韧劲,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零食。虽然不止亏损过一次,但由于赚的次数更多,再加上父亲的经营有度,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家的财富累积到近百万,但父亲铁打的身躯,却再也直不起。
他患上了尘肺,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大口地喘气。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拿到最高级别的工资,他总是抢着做打钻工(用风钻在石头上钻洞的一个工种),几个小时下来,身上满是厚厚的石粉,经年累月,身体终于垮了。但染上了尘肺后,他还是在外面奔波了好几年,直到三个哥哥都已成家,我也考上了大学。
父亲主持了分家,家里三千平方米的大宅子,二哥三哥每人一半,大哥和我各占一个套间的永久使用权,给大哥和我各支付一套城里房子的首付,另给二哥三哥各一笔启动资金,大哥和我因学业过长耗费的巨额资金无需偿还。四个儿子,父亲一碗水基本端平了,于是我们的分家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没有其他分家的胡搅蛮缠,哭天抢地。
从此父亲大部分时间寄居在温暖的南国,但他并没有因此闲下来,洗衣做饭扫地接送孙辈,每天总在忙忙碌碌,他甚至用我给他买的电动轮椅前后载着孙子和孙女赶着去上学,摔破了膝盖也在所不惜。他谨遵医嘱,早睡早起,适度锻炼,不吃腥辣,不涉烟酒,他珍惜半丝粒米,基本不买新衣服,说没多少日子了,不要浪费钱,也总是教导我们“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同批病友陆续离世,而他依旧在勉力坚持,只因为我还没有成家。每次我去看他,成家永远是最重要的话题,他甚至威胁说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但每次总是笑脸迎我,笑脸送我,虽然我也一直在为此努力,但却迟迟未能如愿。后来我甚至想着,或许这是老父亲唯一的牵挂了,我一直没成家,他就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2013年腊月,六十六岁的父亲再一次倒下,虽然此前每年他都会住院一两次,但这次熟悉的主治医生不停地摇头,肺功能完全丧失,肺大泡随时破裂,肺心病随时发作,家属做好准备吧。可吸着氧的父亲明明神志清醒,表达如常呀,一而再,再而三确认,我们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时间不多了,一家人挖空心思若无其事地问父亲还有什么心愿,父亲说想回老家,事情不用大办,一家人要团结,要照顾好母亲。后来又想了想,说老三腊月二十五搬新房子,等给他热闹热闹再回吧。但医生和我们说想回老家就尽早走,不然就可能走不了了,可谁也不忍心走呀。直到腊月二十三日,眼见着病情没有起色,父亲说回家吧,老三就不用跟着回了,搬完新房再回来吧。随后,一生刚强的父亲轻轻地对三哥说:对不住呀,这次不能给你去贺喜了。
一千六百里归途,一路上父亲总是静静躺着,直到进了县城,父亲倚在母亲背上,贪婪地看着家乡的一切,其间,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一生,辛苦您了。
老宅的大门敞开着,只是,这次他的主人再也不能意气风发地迈进家门。家乡的阳光照在床上,父亲喝了几口家乡的水,躺在我的怀里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只能拼命点头,您放心,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满屋的哭声中,我轻轻将父亲放下,我知道这个时刻我不能悲伤,父亲的黄金之路已经走完,而我的新使命刚刚开始……
父亲已经走了六年,我愈发地想念他,刚开始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是笑着的,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我想父亲留给我的除了欢乐,勤俭,更有坚强。不久后,我将带着妻儿,回到他一手打造的老宅,亲口告诉他这些年的这些事,我知道他已经无法知道,但我想让他知道。
- 下一篇:回忆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