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沟村轶事
□ 文/叶丽明珠(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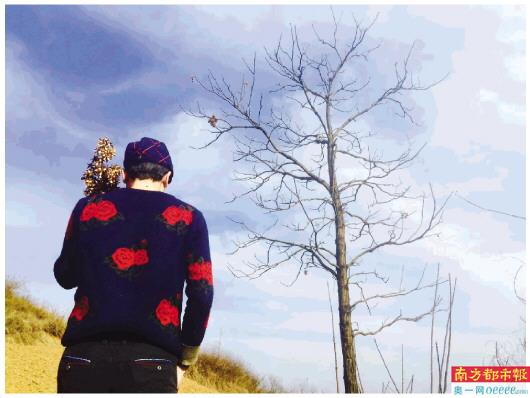
拐沟村是位于秦岭山脉的一个小山村。 作者供图
编者按:南都语闻“回乡笔记”征文自年前启动以来,已收到投稿千余篇。下面这篇,写了村庄里的几个人和事,写出了他们的生老病死,命运起伏。
在纵横千百里的秦岭山脉里,拐沟村是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没有旖旎秀丽的风光,也没有如雷贯耳的名气,但它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祖辈十代人繁衍生息的热土。因为村庄位于曲折交错的几条山沟里,故形象地得名拐沟村。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人们日复一日地去工作,日复一日地笑、抱怨、买东西、吃饭、睡觉。”电影《大鱼海棠》里开篇,一百一十七岁的老妇人追忆往事,发出如此感慨。拐沟村的人们,为了生计,奔波四方,大概也是如此。今年春节,外界疫情凶猛,我的故乡却相对安静。因为道路封堵,假期延长,我得以从容地留守下来,听闻到一些世易时移、物是人非的旧谈轶事。
乡镇书记家的少爷失踪了
我对叶小虎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的少年时代。相比他的名字,人们更频繁地叫他“书记家的少爷”。
小虎的父亲叶梦晋是乡上的书记,写字潦草,但肚有文墨,记性颇好,虽然只读了两年初中,却因写得一手好材料,后来就转正当了书记。
小虎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模糊地记得,小虎长得倒是可爱,圆头圆脑,个子不高。不过,村中人评价,这个孩子脑子不够使。这导致他读书时成绩一直不好,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到广东打工。后来父母千方百计,为他娶了个媳妇,却没怀孕。
自从多年前出门打工以后,小虎就失踪了。
有人为小虎叹息,顺便为他假设了另一种人生:娶了媳妇以后,父母应该把他留在家里,供吃供喝,但不可以赌博,烟可以吸,酒可以喝,整天好玩好逛,愿意动弹就可以给家里搭手种点庄稼,不愿意动弹就算了,不要太指望他。这样,他可以和媳妇生个孩子。那么,对他父母来说,儿辈不行,孙辈可能会行,先人坟上又可以冒青烟。
小虎失踪后,他家攒下那么多钱,最后没有了继承人。小虎的媳妇改嫁了,两个姐姐出嫁后,婚姻都不如意,没有稳定工作。人们欣慰的是,他大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小虎的失踪,无疑给了父母很大的打击。叶梦晋退休后,闲居村中养老。他在某年正月初四去世后,因村里人都不愿意去帮忙料理葬礼,直拖到初十,大家才被召集起来,一起终于把叶梦晋埋葬。
举家躲债的人
我与叶广达已经好多年不曾见过面了。一是我自从十岁开始离家求学,与故乡日渐疏远。二是叶广达全家经常在外躲债。
叶广达的年龄虽然比我大很多,但在村中的辈分却比我低。他在参军退伍后回家务农,与哥哥家相邻而居。他家的债务,主要是因为与哥哥家争强斗胜而引发的。
按照农村土地现行政策规定,叶广达全家四口人,只能批四间房的地基。但是为了占据一大块好地基,并且房间数量超越哥哥家,他执意要争取有六间房的地基。有人劝他在县城买点房,在村里少修点。也有人出主意,建议他把全家的户口本分开,老两口各跟一个儿子,分成两个户口本,写两份申请,填两份表,就有可能获批到六间地基。
拐沟村这些年的巨变之一,就是原来那种砖瓦土木结构的民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楼房拔地而起。叶广达家的楼房矗立起来了,三四十万元的债务也应运而生。本来,他家修房的时候,自己存款只有三万元,只买了所需的砖,就没有钱了,其余的钱都是借的。
“秦始皇曾经统一六国,叶广达厉害啊,如今一次修了六间楼房。”我不知道叶广达听到这样的玩笑,当时有没有笑出来。据说,除了房子的欠账,叶广达被人欺骗上当,也折了一笔钱。另外,他家也遇到过不少花钱的事情。
叶广达的小儿子,在出生后身上长了许多肉瘤,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个包块,从小常被村里人叫“洋芋包”。为了去除那些肉瘤,叶广达带儿子在全省多家医院做过手术,花费不少,并且这些费用不能纳入合作医疗进行报销,每次只能自掏腰包。
为了这个小儿子的婚事,叶广达家连续两次落入骗婚集团的陷阱,不仅人财两空,也成为村中人的笑柄。雪上加霜的是,在2019年,这个小儿子患了直肠癌,经过治疗有所好转,但后续依然需要化疗检查。
其余需要花钱的意外事情,在叶广达家还有一长串。比如,他的老伴在家干农活,人力车翻倒,把腿压骨折了。前几年,叶广达在山上伐树时,倒下的树把一位帮忙的村中人弄成了残疾。
我在村中漫步时,站在公路上远远望见叶广达家的楼房,门窗紧闭,没有人烟,门前满是荒草杂芜。这些场景,早就习以为常。并且,村中几乎没人知道叶广达家人的电话号码,只有传闻他们全家一直在外打工,也算是为了躲债。
“他家的那些债,可能还没有还清,不然就会回家过年了。”在今年格外冷清的春节里,有人猜测年近七十岁的叶广达,带领着打工的家人们,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债务后回到家里。
十八万元的命价
菊,死了,不是死于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飞来横祸。
菊的娘家,不知在何处。许多年前,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拐沟村,衣衫褴褛、神情呆滞。没人知道她来自哪里,没人知道她的年龄和姓名,就随口给她取了个名字,从此人们叫她菊。村中一位曾经被打倒的“地主二代”,同样孤身一人,和她组成了一个家庭,生育了一儿一女。
在菊的后半生,丈夫离世,女儿出嫁,严重结巴的儿子常年在外漂泊,少有音信。她家的房子,是村里仅存的几座砖木结构的老屋之一,破败又脏乱,少有人去光顾。
明显的智力缺陷,导致了菊行动迟缓,缺少语言能力。没人照顾的日子里,好在村人们待她甚好,也算不缺吃穿。就像城市里的人们总惊讶于街头乞丐们顽强的生命力一样,菊在村里也算活得够久。年复一年,很多人被疾病和意外夺走了生命,但要不是那场车祸,人们估计菊可能还要活上好多年。
那是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距离春节还有大约半个月,当天镇上逢集,天气有些阴冷,人们趁早往家里赶去。菊也从镇上的集市向十里外的家中走去。那天,她从家里背了一点晒干的狗腥草去镇上卖。狗腥草可以入药,生长在村里村外的山沟里。不种庄稼的菊,除了在村中串门,还经常去采集狗腥草、蒲公英、柴胡等草药,拿到镇上卖了以后可以换点粮油。其实,前几年村干部已经给菊办理了低保,安排了扶贫户,每月有养老保险,勉强也能过活日子。
阴差阳错地,那天下午回家的途中,天色渐暗,菊迷路了。走过几十年的路,竟然被她忘记了方向。在那个三岔口,她拐上了一条陌生的乡村公路,一辆疾驶的摩托车迎面而来……
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震慑住了那个本来想要逃逸的肇事者。那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老年人,一阵惊慌之后,发现菊没有断气,就喊来熟人把菊送到六十里外的县医院抢救。熟人刚好认识菊的女儿一家,也对菊有印象。
消息传回了村里,菊夫家的族人集合起来,选出几位代表,赶到医院,看到菊已经不行了。肇事者的儿子,是县里的一名年轻公务员,代替父亲在病床前照顾着菊,包括倒尿瓶子。当时的菊已经脑死亡,但心脏还在跳动。
族人在病房外说,生命最后时刻的菊相当于认了一个大儿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她一个星期后,直到她断气。菊的亲生儿子,反倒不曾那么对待过她,漂泊在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生命赔偿费加上丧葬费,肇事者一共交给了菊的儿子十八万多元。菊的葬礼隆重而热闹,流水席办起来,乐队奏起来。她身穿很高级的寿衣,躺在泡桐木棺材里,全村人为她送行。
如果不是死于那场飞来横祸,而是死于寿终正寝,菊的葬礼又会是如何呢?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