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其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现身2024南国书香节,与岭南读者畅谈“大运河”秘史
茅奖作家徐则臣:纯文学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徐则臣,著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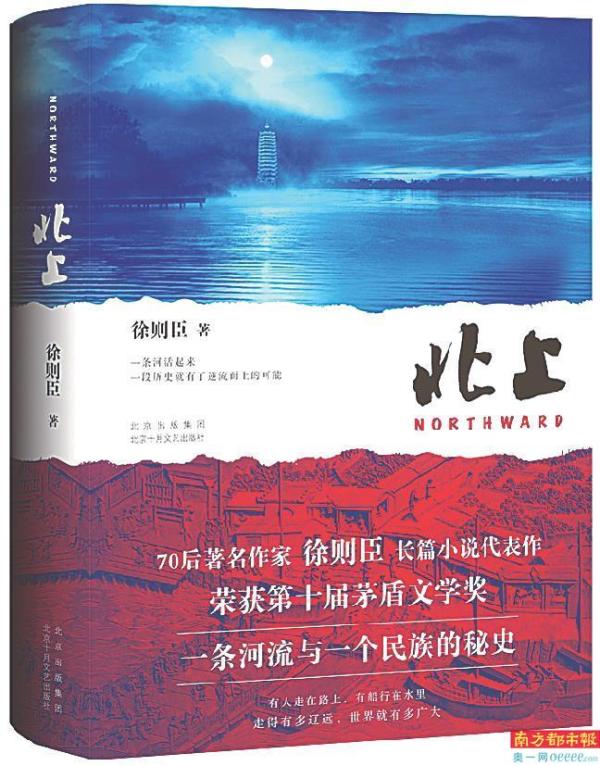
2019年,徐则臣以长篇小说《北上》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折桂中国文学最高奖项对一个青年作家意味着什么?如何在顶峰之后持续探索更广阔壮丽的文学风景?
8月17日,在2024年南国书香节期间,“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读者见面会”在广交会书香节主会场举办。围绕《北上》的写作秘辛和自己的文学道路,徐则臣与现场读者开展了交流。
《北上》是徐则臣砥砺四年、潜心创作的长篇代表作。小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称:“在《北上》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徐则臣从小在河边长大,他的文学生涯与大运河渊源颇深。无论是早期的“花街系列”,还是2015年为徐则臣摘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长篇《耶路撒冷》,字里行间都隐伏着大运河水汽氤氲、明亮浩瀚的身影。在《北上》中,被作家观察已久、沉思已久的大运河终于从背景走到了前台。徐则臣说:“大运河是通向未来的一条河流,通向远方的一条河流。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在他眼里,大运河勾连了历史、现在和未来,它“瞻前顾后”,也“承前启后”。当一行人沿着一条河向着未来走,“这本身当然是一种冒险、一种探究,同时也是一种寻找”。
《北上》之后,徐则臣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融合创新方面大胆尝试,自言现在写作“更自信也更自由”。8月17日当天,徐则臣以“鹤顶侦探”系列之《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在广州还领取了第八届花城文学奖之短篇小说奖。
他笑言广州是自己的文学“福地”,十几年来,他已在广州收获过好几个文学奖项。“这两年写得非常少,所以写一个小说,有动静,有反响,说明大家也关注到了,那就是暗夜行路,你能听见了呼应。”徐则臣感叹道。“这对写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件很温暖的事儿。”
南都专访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徐则臣
这两年写作更自由也更自信
南都:2019年你成为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五年过去了,你觉得跻身茅奖作家对你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徐则臣:我没觉得有多明显,或者说足以改变我的生活或人生轨迹的影响。对我来说写作是业余的,我有全职工作,一周五天班,每天忙得要死。写作的时间很少,一年就写一到两个短篇,都是过年放假的时候写。连着好几年都是这样。一年也就两万字的小说产量。
手头现在有好几个东西,如果给我时间,可以随时开工。我没能力课间十分钟也可以用电脑噼里啪啦敲上一段。我写作需要大块时间,我喜欢沉浸式的写作。
南都:茅奖这种顶级文学奖项会给你的心理上带来压力吗?
徐则臣:没压力,反倒是一个解放。到今年我写小说已经27年,对文学有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写作也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本身就不是一个奖所能左右或者改变的。获奖之前和获奖之后,作品都是那个作品,不会因为获奖,作品的价值就绝对地提升了多少。但我的确更加自信了。
《北上》之后没写长篇,但短篇小说,无论是“鹤顶侦探”系列,还是今年马上要出版的、背景放在海外的“域外故事集”,变化都非常大。跟我过去的小说很不一样,引入了很多东西,甚至短篇小说的观念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些改变要是发生在早几年,是难以想象的。获奖之后,我觉得在写作上应该有新的一种样态,对先前的写作有些审美疲劳,此外,我对文学的很多认知也在改变。既然有新的想法,我努力把它们付诸实践,通过小说呈现出来。所以这两年写作更加自由,也更加自信。过去写一篇小说,别人看不懂或者不熟悉,觉得有点怪,我可能心里会打鼓,现在我可以一直往前走,更放松,也更加关注文学本身。
在《北上》之前已经写了运河许多年
南都:你的茅奖作品《北上》是你的第一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请谈谈写这部作品的缘起。
徐则臣:我写它水到渠成。我小时候生活在河边儿。水是我日常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我最熟悉的身边环境之一。
念初中时,学校门口有一条石安运河,是江苏境内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我们天天在河边玩儿,跑来跑去。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只在杂志上发过,一开始的题目叫《河水向西》,因为石安运河是从东往西流的。写的时候是2002年,我刚进北大,也就是说从那会儿起我已经在很认真地写河流。我在淮安待过,京杭大运河是穿城而过,离我读书和教书的地方很近,我很熟悉。我的短篇小说比如“花街系列”,刚开始那条河已经是小说的一个背景。所以在《北上》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好多年运河。写多了以后,你对它的理解会更加宽阔,也更加深入。你就慢慢对它好像有一种责任,而且这条河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详细,慢慢地它就从后台走到前台来了。
《耶路撒冷》写完以后,效果还不错,很多朋友挺喜欢。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天,聊《耶路撒冷》,朋友说,小说里的运河写得非常精彩,但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下运河?她一说,我挺激动,我脑子里迅速展现了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全貌。我当天回去就把《北上》的结构提纲列出来了。现在还存着当时的笔记。
可能我这么多年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但是在潜意识里一直在组织一个关于运河的长篇小说。因为每次写运河上的故事,都会考虑到运河在故事里能起到什么作用,运河的历史跟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反复考虑之后,这个背景跟历史、跟现实,跟你想表达的其他很多东西慢慢地就建立了联系。过去是琐碎地、零散地在思考运河,现在突然要写它,星星点点的想法一下子就聚合起来,连缀起来。我也很惊喜,觉得可以动手写了。
用外部视角打量运河和历史
南都:为什么把小说的叙事设置在1901到2014年这个时间段?
徐则臣:这就是我长时间用运河作为故事背景带来的“福利”。比较了解了,你就知道运河在历史上起到过什么作用,你也会知道,在写某一段历史时该怎么去呈现运河跟历史的关系,怎么让一条运河作为线索把整个一段历史给勾连出来。
我对晚清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平时看的东西比较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看这几点:我对运河有感情,我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我又希望用运河这样一个极其具有局限性的方式来呈现我所理解的历史,作为一个作家所面临的挑战,真的让我特别兴奋。所以我想,就从晚清写起。
为什么写到2014年?因为写到最后我发现,这么伟大的一条河流自身是不能说话的,它还是需要一个仪式性的东西。结尾在哪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必须是能够提醒我们重新去打量历史,重新去打量这条运河的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申遗成功。
另一个原因,在写作过程中我请教了很多人,他们很多是跟运河申遗有关系的。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也提醒了我,申遗成功这个时间点对运河的再生,或者重新唤醒运河是多么重要。那不妨就以这个时间点为结束。我没想过写一个应景的东西,不会去写,也写不来。最后一看,一百多年,而这一百多年基本涵盖了晚清以来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段。
南都:写百余年的运河史及家国史,为什么要引入小波罗这样一个外国人的视角?
徐则臣:那些年出国比较多,经常会想,一段历史或者一种现实,甚至一个城市,如果换一种目光看,它会是什么样子?平时在国外跟人交流,你会看到同一件事儿,别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跟你完全不一样,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即使没有道理,跟自己的有差异性,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启发。我一直想把这些差异性表现出来。
《北上》刚开头,写不下去的时候,我转头又写了另外一个长篇《王城如海》。《王城如海》也引入两个新视角,有一个英国教授,还有一个海归的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那时候我已经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了。有了《王城如海》作为铺垫和训练,再写到小波罗这样的人物形象,相对就比较得心应手。写作是循序渐进的,很难随便就来一个90度的陡转,也很难开天辟地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它肯定是在某个写作向度上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往前走的。很多人谈《耶路撒冷》和《北上》,往往会忽略《王城如海》,其实《王城如海》对《北上》这个小说而言很重要。
大运河通向远方和未来
南都:如果说大运河体现了一种精神,你觉得是怎样一种精神?
徐则臣:首先大运河是通向未来的一条河流,通向远方的一条河流。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这条河不是今天才开始流动的。从夫差开凿运河算起,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年。这2500年里沉淀了很多故事。它跟这个国家,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它是一个倾听者,也保存、创造和成就了很多故事。
你能沿着一条河向着未来走,去探寻很多可能性,这本身当然是一种冒险、一种探究,同时也是一种寻找。它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意象。
南都:据说写《北上》之前的四年时间,你沿着运河从南往北走了好几趟,去采风搜集素材。这些田野考察具体有什么收获?
徐则臣:一个就是你到了具体的河段,你对这条河的理解更加感性了,更加形象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写小说需要细节,细节越感性,越有意义。另外,运河从南到北的流动过程中,对外行人来说,的确有很多水利上的、河道治理上的难点。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比如说南方的盘坝到底是怎么盘的,三闸两室调节水位到底是怎么调节的,船如何从低处往高处走,它怎么实现水位提级?有些东西就是必须亲自去看才能解决。
在整个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偶然的事件出现。小说中很多细节和故事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比如说考古,当时我想写一个沉船事件,但是沉船里有哪些珍贵的东西,本想泛泛地写一下。正好写的时候去了一趟河南汝州,看了汝瓷,跟一个大国工匠聊天,一下子对汝瓷感兴趣了,就把汝瓷写进了小说。这些东西纯粹是偶然的意外收获。
现在写过《北上》之后,无论是写我自己的生活还是写跟我相近的生活,我都要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已经尝到了甜头。做过田野调查,再写的时候,你下笔会特别自信和笃定。第二个,再熟悉的东西,你认真去看,依然会有发现。你如果以一种研究的方式去看,你会发现“熟悉”还是不够的。你必须盯着它看,如果仅仅是熟悉,写出来的细节也就让人觉得还不错,但如果你认真研究过,很多非常鲜活的小细节大家会感叹:精妙!
南都:现在回过头去看,《北上》还有没有让你觉得不够完美的地方?
徐则臣:我不太重读自己的东西,但是即使不重读,当时写完了我也知道,里面有很多遗憾,但是没办法,在当时我改不了。只要不是硬伤,我也不太想以现在的眼光或者现在的方式把作品再修改一遍。我希望作品跟我那个时候的年龄,跟我当时的阅历,对世界的认知,是相匹配的。
纯文学要寻找新的生长点
南都: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也是你斩获茅奖5周年。你觉得大运河还有哪些故事值得书写?
徐则臣:“鹤顶侦探”这个系列就是发生在运河边上的。运河边上有个小镇叫鹤顶镇,以镇派出所所长的视角去写他经历的案件,这些案件基本上跟运河都有关系。现在写了五篇了,要写十个左右。
我还在准备跟运河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长篇。也是以运河为主角,区别在于,《北上》是沿着运河走,是动态的,这个小说是运河在动,但叙述场景是相对固定的,是静态的。过去是跟着运河看运河,现在是待在一个地方看运河。
南都:最近几年你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花街系列”“京漂系列”“运河系列”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鹤顶侦探”系列。请讲讲这个系列的写作心得,严肃文学作家写侦探小说会有哪些不同的考量?
徐则臣:我觉得可能跟我对文学的认识有关系。我觉得现在所谓的严肃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饱和期。它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可能差不多了,空间愈来愈小,很多桥段、手法、思路越来越趋同,腾挪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当下的文学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厌倦、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时候,它必须经历一个“破”的过程,“破”了再“立”。“破”的话要引入一些新的东西,要给它找新的生长点,要旁逸斜出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类型文学,通俗文学,都可以作为严肃文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比如说这几年的科幻。我们过去觉得科幻就是硬科幻,就是科学的、技术的叙事,它是非常小众的,需要有科学的背景才能看得明白。但是现在科幻和纯文学的嫁接已经非常成功,很多科幻作家处理的,完全是现在的纯文学要处理的,但是在现在的语境下,在现有的纯文学的手段和尺度内处理不了的东西。他们处理的是非常宏大的,有整体观的,甚至有全人类的宇宙观的大问题。在这方面,纯文学里已有的游戏规则是不好使的,反而科幻里更好使。比如网络文学里有架空、有穿越,因为它更加灵活,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比纯文学更方便。有些东西纯文学只能用干巴巴的道理来讲述,用故事是表现不了的,因为它要的是现实的逻辑,就像古典戏剧要遵守“三一律”,只能在这一套规矩里施展拳脚,受到很大的限制。
当然,我也不是说引入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一定就能给纯文学带来新生。在目前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尝试。而且我也不认为,我把科幻、悬疑纳入到纯文学里,就让纯文学变LOW了。
纯文学不是铁板一块,不应该画地为牢。所以我做了这样一个尝试,而且目前看来还是有效果的。我没有过分地在故事上讲究匪夷所思、跌宕起伏,“路转溪头忽现”,我没有搞花哨的东西,侦探只是一个外壳,我还是想解决纯文学解决的那些问题,就是人物的内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的不得已等等。
南都:你觉得自己对侦探文学这种文体有哪些改革和开拓?
徐则臣:我是希望在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两者之间做一个融合。比如看艾柯的《玫瑰之名》这些作品,你也不觉得他写的是通俗文学。他探讨的很多都是非常复杂的、高级的命题。比如帕慕克、多丽丝·莱辛、保罗·奥斯特、阿特伍德、冯尼古特,也都做过这样的尝试。
另外我这些短篇小说都很短。我现在的小说很少超过一万字。我的观点非常粗暴,就是长篇要长,短篇要短。我希望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行了。写短的时候要照顾很多,首先要把没用的、无效的删掉,同时要改变很多叙述的方式,甚至故事的形态,只要篇幅足够短,都得发生变化。而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你对短篇小说,对讲故事,甚至对故事概念本身都会产生全新的理解。
南都:“鹤顶侦探”这个系列的小说收到的反馈如何?
徐则臣:这个系列五个小说里发了四个,《丁字路口》《虞公山》《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和《船越走越慢》,好像这四个全获过奖。《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刚获了花城文学奖,前两天公布的高晓声文学奖也榜上有名。
南都:你对广州这个城市以及广州人有什么印象?
徐则臣:广州我去得不是特别多。但广州在文学上是我的“福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我拿过两次,一次新人奖,一次年度小说家奖。也获过《作品》杂志的散文奖,还获过一个手稿奖,广东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
我特别喜欢在冬天去广州。到了那边植被丰肥,枝繁叶茂。我原来身体不太好,冬天会咳嗽,一到广州就好了。
南国书香节徐则臣推荐书单
《信任》 [美]埃尔南·迪亚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
《烈焰焚币》 [阿根廷] 里卡多·皮格利亚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
《鳄鱼》 莫言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
《河流是部文明史》 劳伦斯·C·史密斯 中信出版集团 2022
《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 王尧 译林出版社 2024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